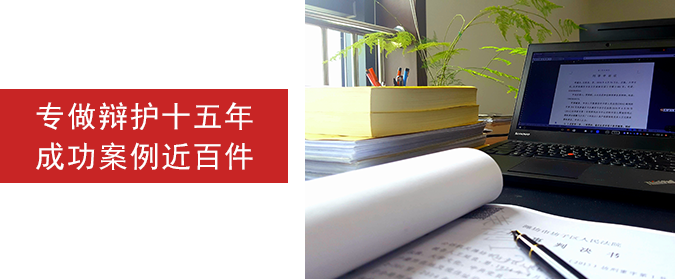朱某涉嫌拐卖儿童罪案辩护词
朱某涉嫌拐卖儿童罪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陪审员:
山东求是和信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朱某亲属委托,并经朱某本人同意,指派我担任其辩护人,依法履行辩护职责。通过庭前的会见、阅卷等工作,并参加今天在审判长主持下进行的庭审,我对本案事实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现根据本案事实和有关法律规定,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一、被告人李某、任某、刘某系因生活困难迫不得已送养婴儿,不具有非法获利目的,依法也不应当以拐卖儿童罪定罪处罚:
2010年3月15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2010意见》”)第16条规定“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亲生子女的,应当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但其第17条同时规定:
“要严格区分借送养之名出卖亲生子女与民间送养行为的界限。区分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获利的目的。应当通过审查将子女“送”人的背景和原因、有无收取钱财及收取钱财的多少、对方是否具有抚养目的及有无抚养能力等事实,综合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获利的目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属于出卖亲生子女,应当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
(2)明知对方不具有抚养目的,或者根本不考虑对方是否具有抚养目的,为收取钱财将子女“送”给他人的;
(3)为收取明显不属于“营养费”、“感谢费”的巨额钱财将子女“送”给他人的;
(4)其他足以反映行为人具有非法获利目的的“送养”行为的。
不是出于非法获利目的,而是迫于生活困难,或者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私自将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送给他人抚养,包括收取少量“营养费”、“感谢费”的,属于民间送养行为,不能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对私自送养导致子女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符合遗弃罪特征的,可以遗弃罪论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可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参与起草《2010意见》司法解释的法官周峰、薛淑兰、赵俊甫撰写的《<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的理解与适用》(《人民司法》2010年第9期,见参考资料)一文,对上述司法解释条文可以做出如下解读:
第一,并非所有的将亲生子女送人并收取钱财的行为都属于“买卖亲生子女”,构成拐卖妇女、儿童罪,也可能属于不构成犯罪的“民间送养行为”;
第二,“买卖亲生子女”和“民间送养行为” 区分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获利目的;
第三,判断是否“具有非法获利目的”的标准,不是单纯“有无收取钱财及收取钱财的多少”,而是“应当通过审查将子女‘送’人的背景和原因、有无收取钱财及收取钱财的多少、对方是否具有抚养目的及有无抚养能力等事实,综合判断”;如果明显是迫于生活困难(如未婚先孕、家庭遭遇重大变故导致生活困难),私自将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送给具有抚养目的和抚养能力的他人抚养,包括收取少量“营养费”、“感谢费”的,属于民间送养行为,不能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
第四,判断是否属于“为收取明显不属于‘营养费’、‘感谢费’的巨额钱财将子女‘送’给他人”,一方面要看收取的钱财是否明显超过了抚育、抚养成本或感谢费的范围,另一方面不能唯数额论,对于那些收养方经济状况较好,自愿支付数额较大的感谢费,而送养方并没有明显讨价还价的,也不应认定具有非法获利目的。
结合本案相关事实看:
(一)李某、任某和刘某均明显不属于将生育作为非法获利手段,而是因为意外怀孕且遭遇了特殊的生活困境,不得已而为之:
二者均属于未婚先孕、意外怀孕,且不敢让父母知道;均是遭遇经济困难,其均身患疾病;也都是因为以上这些因素的叠加,导致未能及时打胎,错过了打胎的时机,才产生了把孩子生下来送人的想法。
其中,李某是因为从事特殊行业意外怀孕,怀孕时才19岁,且患有严重甲亢疾病。怀孕导致其无法再从事以前的工作,失去收入来源,并欠下债务。意外怀孕的事她也一直不敢让家里知道。直到怀孕七个月时,父亲知道了她怀孕的事,带他去医院检查,但已经无法做流产手术。只能把孩子生下来送人,同时也期望能从收养方那里取得一些经济补偿以偿还债务和改善一下生活状况。
任某和刘某是男女朋友关系,两人一起在外租房子同居。刘某开火锅店倒闭,欠下很多钱,被债主索债,被迫借网贷、高利贷,拆东墙补西墙。债主不仅找刘某、任某索债,还找刘某母亲索债,刘某的母亲被逼得想要自杀,刘某也起了轻生的念头。任某意外怀孕时,也只有21岁。因为任某怀孕,加上身患肺病,任某不能上班,刘某也不能去上班了在家里照顾任某,而且刘某也患有胃病,二人都一直吃药。怀孕的事情,任某一直不敢告诉家里,刘某的母亲也不知道。债务、房租、药费、没有收入,经济压力可想而知,加上两人都身体有病,孩子生下来也无力抚养,于是产生了那孩子送人抚养挣点钱缓解生活困境的想法。辩护人看了任某和刘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能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处境的无比艰难,这是一对快要被生活逼疯的年轻人,他们能够如此艰难、如此努力地活下去,就是奇迹。
因此,他们都不是为了卖孩子而怀孕生孩子,而是意外怀孕,在无法打胎流产的情况下才把孩子生出来,收取钱财也不是为了牟利,而是为了给孩子找一个好人家,借此缓解一下自身所面临的的巨大的经济和生活困境,能够活下去,依法不应当认定为为获利而出卖亲生子女。
(二)李某、任某和刘某均是在了解了收养方具有收养目的和收养能力后才答应将孩子送人的:
根据安某、李某、任某的供述,在安某同李某、任某通过微信商谈孩子送养事宜时,李某和任某都向安某了解过领养方的基本情况,安某也告诉他们收养方都是有正式工作和稳定生活来源的上班族。由此可见,李某、任某和刘某,并非不管孩子的死活,只顾收取钱财,同时也关心孩子的未来成长。
(三)李某、任某和刘某收取的钱财数额并不过高,没有讨价还价,收取的钱财主要用于偿还债务、改善生活、孝敬父母,没有肆意挥霍
李某从安徽广德跑到潍坊来生孩子,只收了2.6万元,其中还包括回程路费1000元。2.5万元,作为十月怀胎和剖腹产的营养费和送养孩子的感谢费,数额绝对不算高,且没有任何讨价还价。
李某所收的2.5万元,除了偿还债务3500元,还孝敬奶奶2500元,日常支出一部分,其余的买手机花掉了。年轻女孩喜欢用手机打游戏,也应当算作满足精神生活需要,不是挥霍。
任某收了6万元。安某跟她说生女孩6万,生男孩4万,任某经计算自己和刘某的负债,跟安某要求无论男孩女孩都6万,安某也同意了,这也算不上讨价还价。6万元这个数额作为怀孕并剖腹产生孩子的营养费和送养的感谢费,以及任某刘某在潍坊住了一个月的误工费,也不明显过高。
所收的6万元,还网贷和交房租花去2万余元,孝敬双方母亲2万元,任某买药花去3000元,还个人债务花了一些,日常生活花了一些,任某自己留了5000元。
综合以上事实,辩护人认为,李某、任某和刘某,并非为了非法获利而出卖亲生子女,而是因为未婚先孕、身负债务、身患疾病、无法工作,在多重生活压力和极端困境中无力养育孩子,才不得已把孩子生下来送给有真实收养目的和良好收养能力的人家,且收取的钱财并不过高,没有明显超过营养费、感谢费和其他合理费用的范围。因此,他们的行为依法应认定为民间送养行为,而不是以非法获利为目的买卖子女行为,不应认定为拐卖儿童犯罪。
二、 “领养方”孙某、卢某辉、李某玲、卢某兵、卢某智、付某犯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但犯罪情节轻微,依法应免予刑事处罚:
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第六款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
《2010年解释》第30条第3款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依法免予刑事处罚。”
我国刑法总则第三十四条也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
(一)两个领养家庭都是因夫妻无生育能力,长期多方求子不得,迫不得已才花钱领养:
2011年,孙某30岁,与丈夫结婚,虽然婚后四年一直在家吃药调理备孕,直到现在也怀不上孩子。期间,她和丈夫求子心切,打听福利院,还先后到山东临沂、河南、陕西等地的农村,向找农村家庭困难或者有重男轻女思想的家庭领养孩子,却一直没有找到。
卢某辉、李某玲夫妻结婚六七年,因妻子李某玲身体原因无法生育。为此李某玲精神压力很大,对公公、婆婆和丈夫卢某辉说再生不出来就不拖累他了。公公卢某兵觉得媳妇李某玲人好,也怪可怜的,跟卢某辉的感情也一向很好,不想拆散他俩,于是跟亲家两家人商量好如果碰到生了小孩不想要的就花钱领养过来。
(二)两个家庭经济条件都较好,足以为孩子成长创造良好的条件:
孙某本人干个体,其丈夫是银行职工,收入都不算低。
卢某辉、李某玲家庭也很不错,而且有双方父母和家族的支持。
他们能很快筹措十四五万元钱,一方面说明确实求子心切,同时也说明他们有充足的经济条件为孩子成长创造好的条件。
(三)他们与一般收买拐卖儿童犯罪行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是从婴儿的亲生父母那里领养孩子,不是从人贩子手里买孩子,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都显著较轻:
本案中,作为送养方是因为自身遇到了巨大的生活困境无力抚养孩子,为了给孩子找一个好的家庭才把孩子送养出去,对于领养方的两个家庭而言,他们也是在充分了解了孩子亲生父母送养孩子的初衷之后,同时基于自身求子心切,才愿意花钱领养的。
这种送养,与人贩子通过盗窃、诱骗儿童,违背儿童父母的意愿,使孩子脱离父母贩卖给他人为子,在社会危害性性上显著不同。这种不同,我们只要想一想哪些被人贩子拐骗走了孩子的父母的寻亲经历,以及孩子未来不可知的命运,就不难理解。
(四)他们收养孩子后,在与孩子相处的不长的时间里,对孩子视若珍宝,培养了感情;在有关部门找上门来时,也没有任何阻止解救行为:
无论是孙某夫妇,还是李某玲、卢某辉夫妇,在把孩子抱回家后,都非常疼爱,悉心照料,并且已经对孩子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案发后,他们虽然十分不舍,但为了配合司法机关工作,顺从的把孩子交给公安机关和福利院,体现了良好的态度。
辩护人认为以上情节综合起来,足以体现他们犯罪情节轻微,依法可以免予刑事处罚。并且,如果能够对他们免予刑事处罚,也是给了这两对盼子成伤的夫妇以及他们领养的孩子一个重新团聚的机会,有了这次经历,相信他们对孩子会更加珍惜,孩子也可以在他们的关怀和疼爱下更好地长大成人。综合考虑各种实际情况,让他们继续作为孩子的收养人,无论是对孩子还是对他们,都可能是最佳选择。
尊敬的法庭和公诉机关:
送养子女在我国是一种较为多见的社会现象,送养方通常会向领养方收取一定的钱财作为补偿。送养子女现象多发的原因十分复杂,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的赵军教授曾做过专门调查(见参考资料),主要是由于不孕不育、家族遗传疾病、重大变故、生育指标限制、错过育龄以及传统文化影响等原因,使得我国社会存在大量收养子女的刚性需求,同时由于贫穷、超生、未婚先育、吸毒以及堕胎需要开具证明、堕胎费用高昂等一系社会问题导致许多孩子被生下来却无法得到好的抚养。并且,通过福利院等合法渠道收养健康孩子,除了需要缴纳高额的“赞助费”,更需要“有渠道”“运气好”,能得到这种幸运的人少之又少。再加上通常的社会道德观念不会把送养亲生子女同拐卖儿童画等号。本案是由于打拐志愿者的检举和媒体报道而案发,案发当时也曾受到社会关注,但当人们了解了本案的基本情况,社会关注度迅速下降,到现在已经没有人关注这起案子,其原因也在于这种自愿送养领养子女的现象太普遍太正常了,在这样的行为中,我们甚至无法找到一个真正的受害人。
有人以这种行为侵害了儿童的“人格尊严”这种抽象的概念来解释这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但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有些假、大、空。对儿童来讲,生存权、发展权才是基本人权,抛开生存权、发展权评价他人的人格尊严,不是一种爱护,而是一种残忍。法律应当保护的是儿童的最大利益,是否损害儿童的实际生活利益才是判断这种送养亲生子女法益侵害的关键。具体来说,儿童的实际生活利益至少应当包括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结构的完整性、受教育条件、日常生活照顾、亲情体验、潜在发展机会等事关儿童快乐成长、健全人格养成及未来发展的诸多重要生活指标。在传统拐卖儿童犯罪中,儿童监护权的转移是强制性的,这种强制本身即意味着骨肉分离之痛,意味着对涉案儿童在原生家庭生活权利的剥夺,其对涉案儿童实际生活利益及原生家庭的伤害显而易见。但在“送养”亲生子女的案件中,“领养”家庭在包括经济水平、家庭结构、教育条件在内的生活条件,一般都整体优于那些出于各种实际生活困难而“送养”亲生子女的原生家庭。在这种有别于“真正拐卖”的、主动发生的监护权转移中,至少已部分包含了监护权出让方对子女生活条件改善的考量和诉求。更为重要的是,“养父母”为了实质达成其收养子女的目的,对好不容易花钱领养的儿童往往会倾注较多的生活照料和情感投入。与“真正的拐卖”不同,“送养”亲生子女至少存在实质增益涉案儿童实际生活利益的高度盖然性。从严规制儿童买卖的制度设计,对于拐卖儿童犯罪的综合治理当然具有重大积极意义,但不加区分、不留余地地将涉及亲生子女抚养监护权转移的所谓“买卖”行为统统纳入刑罚规制的范畴,明显违背了罪刑均衡、罚当其罪的刑法原则。
刑法是冰冷的,但同时也是有温度的。刑法的温度就在于,它在将以非法获利为目的买卖亲生子女的行为纳入刑事规制的同时,规定了严格的区分适用、排除适用条件,将那些因为实际生活困难、不是为了通过卖孩子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排除在拐卖犯罪之外。同时我国刑法还规定了在案情特殊情况下在法定刑幅度以下量刑的特殊宽宥制度。能否基于本案的特殊情况,本着“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有效地适用这些体现刑法温度的条款和制度,将决定我们的司法是否具有温度,是否真正能够体现刑法的公正和正义。辩护人对此充满期待。
四、在本案送养、领养方不构成犯罪或犯罪情节轻微的情况下,对从中起中介作用的被告人朱某,也应当结合其具体情节依法减轻处罚:
(一)本案整体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对在其中起中介作用的被告人朱某等人应依法减轻处罚:
被告人朱某在这两起事实中起到了牵线搭桥、联络协调等中介作用,且收取了一定的中介费用,虽然可以构成犯罪,应当受到刑事处罚,但通过辩护人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到送养、领养双方的行为一方不具有刑事可罚性,一方犯罪情节轻微,说明本案整体社会危害性较小。在此情况下,对于在其中起中介作用的被告人朱某等人,为了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和量刑均衡,也不适合机械地套用拐卖儿童罪5年以上的法定刑幅度,辩护人建议人民法院依照刑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被告人朱某等人减轻处罚,在法定刑以下量刑。(类似情况下其他法院处理意见见参考资料)
(二)被告人朱某还同时具有以下酌定从宽量刑情节:
1、朱某涉案系应受本案领养方恳求为他们好心帮忙所致:
被告人朱某自身也同样有结婚多年不孕不育,最后通过做试管婴儿才生育子女的痛苦经历。为此她开了一家公司,介绍社会上一些不孕不育的夫妇通过做试管婴儿求子。正是因为她有这段经历,从事这个职业,接触到想送养孩子的信息的机会比较多,长期求子不得的孙某、卢某智等人才找上她,恳请她帮忙寻找这种生下来弃养的孩子。我们不否认朱某具有从中获利的动机,因为从中联系、协调也需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得到一些报酬也是合理的。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朱某做这些事时也是抱着帮助他人的善念。
2、被告人朱某有坦白情节,依法从从轻处罚。
3、被告人朱某有检举他人犯罪,如经查实,依法可减轻处罚。
以上辩护意见,请合议庭参考。
辩护人:山东求是和信律师事务所
律师 窦荣刚
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八日